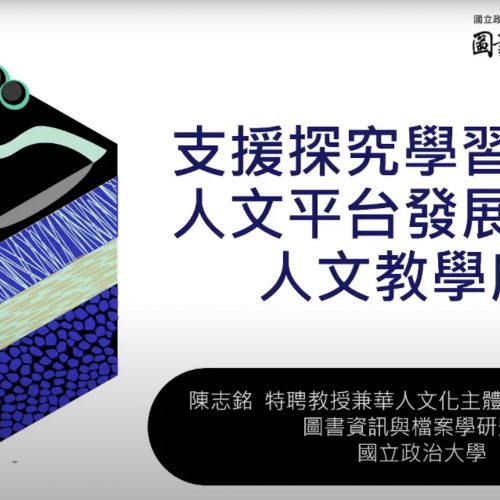本中心於4月19日(一)與日本大阪大學、上智大學學者,進行線上座談,彼時台灣尚未爆發本土群聚感染(台灣於5月19日宣布全面進入第三級防疫警戒),該座談僅為初步對話,尚需視疫情變化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自2020年初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原有的世界與人類發展設想驟然失效,全世界陷入巨大的裂縫之中。病毒侵害人命誠然有其生物醫學的科學原理,但世界各國不同的致病率與致死率,卻是涉及了各個社會不同的文化價值與社會行為。「生活的邏輯」:即卡繆在小說《瘟疫》(The Plague)所指出,社會中每一個人都贊同但卻導致人們喪命的行動與原則。這些原本作為人們生活行動的正面道德與價值指引,在疫病來襲時卻成為為死亡鋪路的陰影。雖然卡繆的警言很難以數據來證成,但每個受衝擊的社會不免需要對其於疫情中失效的生活邏輯加以反思,不僅是為了預防未來,更是為了認識其理所當然之價值限制。」召集人李維倫老師(華人倫理實踐研究群研究員、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以上述開場說明召開會議的緣由,上智大學濱窩教授(Prof. Hamauzu)先介紹上智大學的「悲傷關懷研究所」,如何對失去親人的哀傷進行靈性的關懷(spiritual care),接著提到有學者針對目前為止(4月19日)歐美疫情遠較亞洲嚴重的可能因素,稱之為「X因子」,意即未知原因,可能原因被推測為基因,或以日本而言,強制接種結核病疫苗等,皆有可能。他也提到,100多年前在俗稱「西班牙感冒」(1918-20年)的疫情中,日本曾有2380萬患者和39萬人死亡,儘管如此,2003年的SARS和2019年的MERS都未能登陸日本,2009年流感(H1N1)爆發後,儘管在2012年 制定的《應對新型流感特別措施法》於今年生效,但卻未能得到認真的考慮,以致無法建立充分的制度以因應之。
疫情改變了生活,這段日子以來,雖然視訊可以取代一些知識上的交流活動,免去了交通因素的干擾,但是在溝通行動中看似無關緊要的東西、情感的連結等其實是很重要的東西。另外,濱窩教授提到「遠近法的變換」,意指遠在天邊的人透過網路,很容易就可以連上,但近在身邊的人連結反而變少,尤其是高齡者一旦受到感染,很容易演變成重症致死,2021年3月大阪有超過1100多人感染,其中有七成的人來不及送到重症病房就可能嚥氣,或是當無法呼吸,需要裝上呼吸器時,該由醫師、病人或家屬來決定是否裝呼吸器,也是一個倫理上需要思考的問題。再者,過去戴口罩是為了怕被感染,現在戴口罩是因為怕自己在無症狀感染的情況下,把病毒傳染給別人。這種「感染的反轉」也是一種特別的現象。最後,在視訊會議中,看著螢幕上的自己說話,同時進行著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觀點是個不同的體驗,這種體驗會帶來甚麼樣的改變,也值得討論。

大阪大學的Horie教授回應濱窩教授所言,日本在疫病控制的制度和法律上有所不足的問題。他認為,日本太依賴道德的政治文化,道德畢竟是個人的行動,一旦涉及疫病控制的群體行動時,國家就必須要運用強制性的措施,例如行動的管制和強制戴口罩等,除了強制性的作為外,政府也可以透過補助金讓行動受到限制的人,不管是個人或是企業都可獲得補償;道德規範並非不重要,但必須以法律為條件,才能發揮充分的效果,而法律的規定必須要清楚、完整,不可曖昧不清。回顧日本歷史,二次戰後曾針對結核病採取積極作為,但這也是日本採取強制作為的最後一次,從此之後,日本政府對於疫苗的開發、預防政策的擬訂等漸漸地採取消極的態度,形成一種輕視感染病的「文化」,加上日本政府經常在法令制定上採取一種模糊的態度,以使民間企業有運作的空間,這在戰後扶植經濟上或許有所幫助,但在對抗疫病的攻擊上,顯然受到限制。總的來說,Horie教授認為,在此次疫情當中,日本政府過度依賴人民,然而,道德上的自我約束效果有限,政府在此次防疫的過程中反應顯然過慢。
藍適齊老師(華人思維模式研究群研究員、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提及,除了法律之外,經濟文化的考量是否也在日本防疫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李維倫老師則回應Horie教授,在政府的強制作為之下必須考量的是人權的負擔(human right’s burden),這些因素都使得防疫的工作更加複雜。
本中心博士級研究員高長空則指出,新冠肺炎的全球擴散是科學、科技、政治、經濟等諸多因素的結果,即使是台灣、紐西蘭等防疫相對成功的國家與其說有「共同的」文化因素,不如說是正確的政治決策、善於使用科技和醫療基礎建設。他主張,我們不應該將不可度量的文化面向,與可度量的政治、法律、科學或科技面向對立起來,這些面向無一是自主的,而是在複雜的脈絡中交互作用的。
本中心博士級研究員林淑芬則提及,台灣模式所凸顯的政治與文化具有哪些可普化的面向,是我們可以思考的。有學者以為,COVID-19 疫情凸顯了與樂觀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相伴隨的「存在的焦慮」,這似乎要求我們重新思考另一種全球化的思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對比之下,我們可以如何展望一種不同於過去的全球化文化?另外,令人憂心與不安的是,在歐美地區零星出現的反亞或仇亞的情緒,此一情緒背後隱藏了甚麼樣的不安現象,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總的來說,如果文化指的是一種「生活的邏輯」的話,台灣在這次防疫的過程中,表現出甚麼樣的生活邏輯?這樣一種生活邏輯是否具有可普性? 我們或可將此「生活的邏輯」整理如下,並在防疫過程中或未來的後疫情時代,繼續對其保持思考。
1. 政府信任度:由民主社會的人民所賦予。
2. 專家治理:起因於 SARS 的經驗,非常時期政府的運作模式採用專家治理模式。
3. 採取哪些措施:感染控制、邊境管制、數位圍籬、數位追蹤。
4. 面對專家治理的全面的管控,人民要保持自主性,需要有公開、透明、
正確的資訊(避免造謠),「美玉姨」之類的 Chatbot,便顯得重要,因為資訊必須民主化,政治才能民主化,亦即資訊民主化是政治民主化的條件,然而,此一作法尤其要留心相關資訊以及數據被壟斷或操作。
5. 對數位治理的接受度高未必消極地意味著對隱私不夠敏感,也可能意味著社群有能力賦予科技意義,此一社群的能力似乎依賴著一種社群意識,這種社群意識或社群之間的連結性未必是與自由對立的集體(collective),對台灣社會而言,「自我」的界線或許並不那麼絕對,反而是模糊而可以有彈性的。